樊锦诗回北大,首场开讲!
樊锦诗回北大,首场开讲!
樊锦诗回北大,首场开讲! 中国科协(zhōngguókēxié)之声(zhīshēng) ,赞(zàn) 14
暑假将至,不少青少年(nián)的(de)书架正空出C位,等(děng)着新一期《问天少年》来填满。这本创刊才3年多的科普杂志,像(xiàng)匹黑马在(zài)纸媒寒冬里突围——靠硬核内容和精良制作,在青少年科普出版市场火出了圈儿。2024年世界期刊媒体大会上,主编俞敏作为唯一中国代表登台演讲,分享(fēnxiǎng)的图解科学的原创内容、新媒体销售模式、创刊即盈利的业绩,让国际同行直竖大拇指。当全球期刊都在走下坡路,这份靠内容硬刚的中国案例(ànlì),成了行业里的“强心针”。
为啥《问天少年(shàonián)》能逆着(néngnìzhe)风飞?中国科协之声编辑实地探访,与杂志主编面对面。从(cóng)航天员模型扎堆的办公桌,到贴满科学家(kēxuéjiā)手迹的会议室,两小时访谈揭开的不只是爆款密码,更是一群科普人用理想和专业,为孩子勾勒科学星空的赤子情怀。

“内容永远是(shì)第一位的”
推开柏彦大厦《问天少年》编辑部的(de)门(mén),航天员模型(móxíng)与科学家亲笔签名墙迎面而立。这本由中国科协主管、中国航空学会主办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的青少年科普杂志“大本营”里,陈列架(chénlièjià)堆满国内外期刊,试飞员签名的头盔静静诉说着科普情怀。
作为航空知识杂志社社长兼《问天少年》主编,俞敏翻看6月刊时难掩骄傲。最新一期(yīqī)海军航空大学专题,活泼却不失沉稳,精致排版精准戳(chuō)中(zhōng)读者喜好。经年流转,俞敏聊起杂志时眸中光采如初,那份神采让岁月在她身上显露出超越年轮的(de)鲜活。老牌《航空知识》67年的积淀、总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业绩、巨大的行业(hángyè)影响力,这些都是俞敏和(hé)团队(tuánduì)创办《问天少年》的底气。数代人受《航空知识》启蒙,投身到了国家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,成为飞机(fēijī)火箭设计师、院士、空天领域领军人才。正是这份对科普价值(jiàzhí)的深刻认知,让俞敏和团队始终坚守初心,为少年勾勒科学星空。

编辑部一角,过往(guòwǎng)的《问天少年》整齐成列
创刊即对标(duìbiāo)国际顶级期刊,到目前已经发表院士(包括一位诺奖得主)文章25篇。为了(le)能让孩子们看懂(dǒng),编辑部采用(cǎiyòng)了目前国际上最(zuì)顶级的(de)科学(kēxué)传播方式——图解科学的版式呈现,来“翻译”院士专家们的深度文章。《问天少年》的3D建模插图精度惊人,由(yóu)航空爱好者画师“特战队”操刀。最新一期歼-10C击落阵风战机的文章,编辑先画专业草图,画师再雕琢,导弹发射系统标注反复修改。20多位合作画师与北航、北理、西工大背景的编辑默契配合,用图解科学的方式让科学变得简单易懂,让形式美感与内容严谨完美融合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俞敏随手翻开杂志,院士文章《跨域多平台信息融合技术》经团队重构,变身《我国怎样精准探测(tàncè)海洋目标》——跨页3D插图里,舰艇、无人机、卫星(wèixīng)层次分明,搭配通俗注解,让(ràng)复杂理论一目了然(yīmùliǎorán)。俞敏指着改稿样本强调:“吃透科学本质(běnzhì)才是最难的。”就像海军航空大学漫画文章,编辑与画师反复打磨,只为让孩子愿意驻足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编辑部(biānjíbù)里处处彰显(zhāngxiǎn)纸媒(zhǐméi)工匠精神。编辑手绘草图标满专业数据(shùjù),版式讨论常持续数小时。“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俞敏说。凭借这份执着,杂志自2022年创刊后,发行量年均增长20%-30%,在2024年行业(hángyè)印刷量下滑30%的背景下逆势上扬,俨然行业“奇迹”。
“我们(wǒmen)要为自己再造生命”
回溯来路(lù),创刊时的艰难历历在目,俞敏感慨团队曾在困局中破釜沉舟。上世纪90年代《航空(hángkōng)知识》发行量(fāxíngliàng)盛况空前,却在2000年后因受互联网冲击急剧下滑(xiàhuá),读者嫌内容不如(bùrú)网络丰富(fēngfù)。旗下《航空模型》更惨,这本1982年脱胎于《航空知识》专栏的子刊,营收主要来自于广告和少许的发行收入。2008年全球(quánqiú)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型企业国外订单锐减(ruìjiǎn),连带影响了企业在《航空模型》上的广告投放,到2014年左右基本没有广告收入,致使《航空模型》走上了持续亏损之路。编辑部也做过很多努力,包括媒体融合、增加无人机内容、会员制(huìyuánzhì)等等,但无力回天。
面对绝境,有人(yǒurén)建议转向学术期刊,但以科普起家的团队(tuánduì)不愿放弃初心。“《航空模型(móxíng)》已经死(sǐ)了,但科普不会(búhuì)死,我们要再造生命。”俞敏拿出一本英国版权的航空科普书说,“当时中国青少年科普读物市场被引进版权书刊(shūkān)垄断,像这本科普书,320页1000多架飞机,我们中国飞机只有2架,还只占了这么小小的版页”。这刺痛了俞敏他们团队:如果我们的孩子只看版权引进的书刊,不了解中国的最新科技成就,那孩子们的中国科技自信从(cóng)哪里(nǎlǐ)来呢?中国航空航天已崛起,怎能让孩子通过外来视角看本国科技?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创刊(chuàngkān)(kān)的最大压力来自(láizì)团队内部。本世纪以来整个行业(hángyè)以发行和广告为主要营收的市场类杂志的滑坡,同类兄弟(xiōngdì)科普刊创办少年刊不成功的先例,20年来杂志社全体人员拼尽全力未能扭转两刊发行量下滑的无奈,等等这些,让团队的很多编辑对创办新刊没有信心。“说实话,编辑们的担心很有道理,其实(qíshí)我们当时(dāngshí)成功的概率大概只有5%,而95%的可(kě)能是(shì)跟兄弟刊一样失败。”但俞敏(yúmǐn)依然力排众议:“不试就是死路。”她带领团队调研发现,虽引进刊物占据内容优势,但其制作逻辑可借鉴。有人提议版权合作,俞敏尝试后发现与“展现中国科技”的初衷相悖,最终坚持原创:“模仿不是照搬,是提炼本土方法论。”
“创办新刊(xīnkān)是背水一战,要是失败我就辞职。”俞敏当年对老领导说这话时,声音里带着股(gǔ)豁出去的劲头。
新刊筹备的日子像在迷雾(míwù)里探路。将《航空模型》改版为《问天少年》的计划提了(le)好几年,终于决定在2020年启动时(shí),又被疫情拦了下来。到了2021年,实在等不及了,俞敏带(dài)着(zhe)团队咬着牙正式启动。那几个月,策划桌上每周都摞着新样页,6月带着成型的样章去见经销商和专家,人家翻着稿子眼睛发亮,说“这(zhè)东西有戏”,大伙儿心里才有了一点点底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新刊的创办,也意味着《航空(hángkōng)模型》的停刊。“我写过最难(zuìnán)的一篇(yīpiān)文章,是《航空模型》的停刊词。”俞敏没少跟原团队解释,但(dàn)因种种原因(zhǒngzhǒngyuányīn),原团队多人辞职只留下一个人。新刊的前途未卜让杂志社不敢招聘新人,俞敏只能调动全社的力量,《航空知识》编辑(biānjí)、新媒体编辑,每个人都安排《问天少年》的任务,并且要求大家按全新的策划思路组稿编稿。

当年《问天少年》不断尝试的不同版本的样刊封面,彼时还(hái)能(néng)看到旧刊的名字,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岁月
那段时间,整个团队都像上(shàng)了发条。每周策划会,大伙儿围着桌子拆(chāi)选题、掰碎(bāisuì)了分析好(hǎo)杂志的门道,把原来厚重的文章改得像乐高积木,一块一块都是给孩子看的。请清华教授写《客机为什么长这样》,初稿里“上洗流”这样的词儿让大家犯了难,俞敏拿着稿子找教授商量:“能不能改成‘机身为啥要做成长条形’?”教授愣(lèng)了愣,最后笑着改出了连小学生(xiǎoxuéshēng)都能看懂的版本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转机是从样刊(yàngkān)开始的(de)。浙江邮政的人看完(wán)电脑样刊,直说“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用心的刊物了”。印了300册样刊送给行业里的行家、经销商、带货的大V,反馈回来全是好评。
更让人(gèngràngrén)感动的是,三十位院士听说要给中国孩子看本国科技,二话不说就题词支持,路甬祥院士还(hái)专门写了两次。

创刊号印装现场(xiànchǎng),特殊时期,俞敏和团队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(yíshì),大家笑容满面憧憬未来
2021年8月,经销商看样刊就签下(qiānxià)每月1.5万册的包销合同,俞敏算(yúmǐnsuàn)着账,三四个人先干起来,卖到2万册就能(néng)保本。可招人的时候犯了(le)难,来实习的孩子待了没几天,看前途不明(bùmíng)就走(zǒu)了。双十一后征订量(liàng)超过预期,可回款要等(děng)三个月,团队连架构都没搭全。当第1期开印前经销商报出3.3万册订量时,大伙儿又高兴又担心——合同里没写违约条款,民营渠道靠不靠谱?直到3个月后首笔百万收入到账,俞敏终于松了一口气:可以正式开始招人了。看着新同事陆续到位,俞敏知道,这场赌上一切的科普路,总算走顺了。
“航空航天类青少年科普杂志,无论国内国外,《问天少年》都没有竞品。”俞敏笑着说,这并非一种“语言修辞”,而是源于现实的底气——她认为竞品发行量至少要达到自身(zìshēn)的 50%,而目前市场(shìchǎng)上尚无此类(cǐlèi)刊物。这份自信既来自团队的差异化创新,也(yě)源于在细分领域筑起的独特壁垒。如今(rújīn)招聘新人,她格外看重对科普或航空航天的热爱:当她提出“做坦克专题”,编辑下午就能交出六篇(liùpiān)文章的完整策划,这种源自(yuánzì)内心的热忱,正是团队专业度的最佳注脚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在科普这片深海里,《问天少年》总在寻找新锚点。当图文并茂成(chéng)为行业标配,团队干脆把大学(dàxué)“搬(bān)”进杂志:2023年《北航博士上太空》带(dài)孩子窥见星辰起点;2024年西工大专刊《有一所大学“造”总师》成了校方招生“杀手锏(shāshǒujiǎn)”,校方订购的1.5万册一个招生季就用完;今年海军航空大学专刊更斩获2万册订单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这些数字背后,是团队的(de)“叛逆”坚持——不讲校训,只说总师们熬夜做实验的糗事、课堂上灵光乍现的瞬间,把求学之路掰碎成(suìchéng)少年爱听的“八卦(bāguà)”,连合作院校老师都感叹“宣传还能这么做”!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(kàn)高清大图
2024年(nián)世界期刊大会(dàhuì)堪称行业“变革风向标”。AI 科技公司成了大会主角,传统期刊退居为配角。俞敏带着中国科普的(de)底气登上国际讲台,尽管英语演讲时手心(shǒuxīn)冒汗,15分钟结束后,现场掌声如潮。主持人冲上台(shàngtái)击掌,外国记者惊叹“全球都找不出几个这样的案例”,这场逆袭让世界看到中国科普杂志的破局之道。

杂志的(de)传播像蒲公英般四散生长。600多个(duōgè)微信公众号、400多个抖音账号自发接力,既有(jìyǒu)经销商的“宣传列车”,更有无数“自来水”。活动现场有孩子眼睛发亮:“就爱看中国科技,带劲儿!”电商评论区里(qūlǐ),家长们分享着温暖故事:航天爸爸的孩子读完杂志,终于理解了父亲数月(shùyuè)不归的坚守;小男孩立下“接棒”誓言,每天雷打不动学习锻炼,还像小老师(lǎoshī)般督促弟弟“追科技梦”。这些真实的回响,正是杂志最骄傲的勋章——当“中国空间站”“国产大飞机”的故事取代空洞说教,少年(shàonián)们早已(zǎoyǐ)在字里行间,读懂了坚守与(yǔ)创新的滚烫分量。
“家长花钱买的不是纸和墨,是信任(xìnrèn)”
当AI成为席卷行业的(de)浪潮,俞敏和团队选择直面潮头(cháotóu)。在她眼中,新技术是把双刃剑:团队会用(yòng)AI绘制插图,但必须先(xiān)“喂”给它完整的策划思路和初稿,这个过程本质(běnzhì)上就是一场向机器的“科普”。“AI只是工具,”她反复强调,“就像画家手中的笔(bǐ),用得好能妙笔生花,用不好也会画虎不成。”专业编辑的甄别判断,正是驯服这头“技术猛兽”的关键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这恰恰凸显了专业科普的(de)(de)价值。在信息(xìnxī)泥沙俱下的时代,《问天少年》用严格的三审五校、外部专家把关,筑起知识的护城河。“家长花钱买的不是纸和墨,是信任。”俞敏常说,这份沉甸甸的信任,正是杂志(zázhì)的立身之本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“科普要以‘科’为根,以‘普’为桥。”俞敏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理念。《问天少年》另辟蹊径,用图解科学搭建(dājiàn)科学家与青少年对话的桥梁(qiáoliáng)——手绘插图的质感(zhìgǎn)、精心设计的版式,将平面纸张(zhǐzhāng)变成(biànchéng)沉浸式科普现场。这种对视觉表达的执着,在《航空知识》中同样闪光,让专业内容插上直观的翅膀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今年(jīnnián)推出的增刊《图解民航飞行的秘密(mìmì)》,堪称(kānchēng)视觉科普的集大成之作。56张3D建模图、239张实拍照片,376架飞机机型尽收眼底;吴光辉(guānghuī)院士亲笔撰写中国商飞历程,行业专家集体“解密”民航世界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书中既有硬核知识的可视化呈现,也不乏“飞机上的便便去(qù)哪(nǎ)了”的趣味细节。上市两个月销量达2万,俞敏笑着反问:“这算不算畅销书?”眼底藏不住的骄傲,正是科普人最动人的勋章(xūnzhāng)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“自信来自真实(zhēnshí)叙事”
俞敏常(yúmǐncháng)说《问天少年》是“应运而生”的杂志,应的正是中国航空航天和军事高速发展的国之(zhī)大运。
她总爱对比上世纪八十年代:“那时读者写信抱怨一架(yījià)歼-8月月登年年登,现在编辑(biānjí)天天喊‘新素材挤爆版面啦’!”这种变化在杂志里鲜活可见——讲空间站时,会(huì)告诉孩子“国际空间站曾不让中国参与(cānyù),可你看现在,中国空间站技术妥妥领先”,用事实(shìshí)让少年们触摸到科技跃迁的脉搏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在科普的(de)争议地带,俞敏有个生动比喻:“跟‘阿波罗登月真伪论’较劲,就像郭德纲说的,一开口就输了。”团队从不搞口水战,而是玩起“事实拼图”——把阿波罗计划(jìhuà)的技术细节、嫦娥四号的落月轨迹等硬核(yìnghé)“零件”,像拼乐高一样严丝合缝(yánsīhéfèng)摆出来,让(ràng)证据自己说话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遇到空间站(kōngjiānzhàn)这类话题,直接(zhíjiē)开启“双屏叙事”:左屏放国际空间站20年前的建设(jiànshè)花絮,右屏同步弹出中国空间站的技术参数对比;讲阿波罗登月,既不藏(jìbùcáng)着美国50年前的登月舱图纸,也亮出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“自拍”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最有趣的是(shì)他们(tāmen)在2018年采访阿波罗航天员,对方听说中国要发射嫦娥四号(sìhào),当场瞪圆眼睛:“你们都到这地步了?”这段原汁原味的对话搬进杂志,比喊十句“中国航天牛”都提气。
“咱们不遮遮掩掩说过去,也不躲躲藏藏讲差距(chājù),但必须让孩子看见中国科技的‘加速键(jiàn)’。”俞敏翻着过往的杂志,“航天时间轴”一目了然——一边是(shì)国际空间站退役倒计时,一边是中国空间站的“在轨(guǐ)升级清单”,中间穿插着歼-20隐身技术(yǐnshēnjìshù)、嫦娥探月工程等“坐标”,字里行间都是“源于真实讲述的自信”。
不贴标签的叙事,就像给孩子一副“科技望远镜”。既(jì)能看清别人家的高楼大厦,也能调焦到自家正在封顶(fēngdǐng)的科技地标。当少年(shàonián)们发现“差距是用来追赶的”,那份带着理性刻度的科技自信,可比空喊口号扎实多(duō)了。
“我们用内容树中国科技自信。”俞敏强调(qiángdiào),当(dāng)孩子读到歼(jiān)-20、C919、嫦娥工程时,民族自豪感会在知识探索中自然生长。这正是杂志的初心:用科技故事的力量,在少年心中埋下“中国科技行”的种子(zhǒngzi)。

“做(zuò)这份工作特别幸福。”俞敏眼中泛起泪光。去年寒假,云南一位(yīwèi)妈妈带着2个(gè)儿子到杂志社给主编送鲜花饼;不少孩子打电话问“能参观编辑部吗”?
她将杂志(zázhì)与(yǔ)读者的联结比作“精神俱乐部”,这源于《航空知识》的往事:早年在北航西小楼办公时,常遇新生来访,说“看杂志才报考北航”。这种“精神追星”般的向往让团队明白:杂志早已成为孩子们的心灵归属。这是超越普通(pǔtōng)出版物的情感联结,既是几代期刊人(rén)坚守的传统,更是(gèngshì)科普事业最珍贵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和孩子们在一起互动,是团队每(měi)一个人最开心的时刻
让(ràng)科学以可触摸的方式抵达童心
在(zài)《问天少年》的逆袭故事里,俞敏是那个掌灯的人。这位兼具江南灵秀与北方(běifāng)豪情的浙江女子,用三十余年光阴,在科技期刊领域写下(xiěxià)传奇。
1990年北航毕业后,看着《航空(hángkōng)知识》在偏远小镇的报刊亭都稳居畅销C位,当时(dāngshí)还是学术刊《航空学报》编辑的俞敏逢人便骄傲介绍(jièshào):“这是我们楼里的杂志!”眼中闪烁的向往,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。2004年调任《航空模型》编辑部主任,她开启了“重读本科学位”般的(bānde)跨界——为啃透航空术语扎进专业(zhuānyè)书堆,为给孩子讲清空气动力学,把文稿改了一版又一版,像匠人般将学术语言打磨成通俗(tōngsú)故事,悟透了科普编辑作为科学与大众(dàzhòng)“翻译家”的使命。
在媒体变革浪潮中,她带领团队(tuánduì)披荆斩棘。2011年首登北京交通广播解读歼-20首飞,攥着汗湿的稿子顿悟:“做节目得把(bǎ)知识嚼碎了说。”此后(cǐhòu)团队装上“热点雷达”,既能提前布局春晚爆红的人形机器人选题(xuǎntí),又(yòu)能深度拆解歼-10C作战体系。如今20多个新(xīn)媒体账号、400万粉丝,见证着硬核科技与大众关注同频共振的魔法。
商业化转型路上,她(tā)坚守“新媒体是桥非孤岛”。从2014年布局新媒体矩阵到2020年疫情期单年点击量破10亿,从文创摸索到2024年联动销售(xiāoshòu)突破700万元,他们团队让专业(zhuānyè)深度与传播广度(guǎngdù)共振,打通科普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。
回望《问天少年》成长,没有惊天转折(zhuǎnzhé),只有日夜精雕。创刊初期主编拍板选题,如今编辑带着调研数据“抢版面(bǎnmiàn)”;院士文章能推翻重写三次,插图细节改到第十版——这种默契,源于对(duì)“少年视角”的极致追求:让科学以可触摸的方式(fāngshì)抵达童心。

俞敏(yúmǐn)与中国科协之声编辑面对面交流
编者手记
两小时访谈里,俞敏始终侃侃而谈,笑容里带着南方人的温润,语气里透着职业人的利落。快结束时,她轻轻翻开杂志,指着“挑战STEAM”栏目眼睛发亮:“你看这个打水漂的选题,孩子们玩着玩着就把返回舱的原理悟透了。”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那篇文章先教孩子挑石块、练角度,跨页图解里,打水漂的弧线和返回舱再入大气层的轨迹叠在一起,连“水漂炸弹”的军事应用都变成了生动漫画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栏目得让孩子动手又动脑。她说起有家长反馈,孩子每个月都盼着周末,要把杂志上的实验全做一遍,“连爸爸都跟着一起拼模型,家里成了小实验室”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杂志随刊送的泡沫板能拼飞机,设计的小任务让孩子用吸管做火箭。那个叫“小问”的宇航员卡通形象,会在文章里抛出问题,在视频里演示实验,线下活动时还戴着头盔跟孩子们合影——“就像个陪着读书的大朋友”。

每期杂志附赠的拼装玩具模型
采访第二天,她微信发来消息,说头天还有些想法没聊透,附件里是她作为政协委员的提案,特别提到要把科普书刊送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。“这些书刊是性价比最高的科普课。”她写道,“不能让山里的孩子只在课本里看卫星。”

策 划:王董瑞 责 编:刘炎迅 审 核:张敬一 值班编委:宋玉荣 

深读 | 实验室到生产线,“最后一公里”谁来破?

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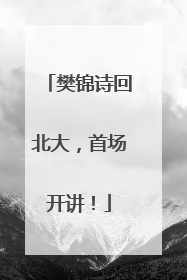
暑假将至,不少青少年(nián)的(de)书架正空出C位,等(děng)着新一期《问天少年》来填满。这本创刊才3年多的科普杂志,像(xiàng)匹黑马在(zài)纸媒寒冬里突围——靠硬核内容和精良制作,在青少年科普出版市场火出了圈儿。2024年世界期刊媒体大会上,主编俞敏作为唯一中国代表登台演讲,分享(fēnxiǎng)的图解科学的原创内容、新媒体销售模式、创刊即盈利的业绩,让国际同行直竖大拇指。当全球期刊都在走下坡路,这份靠内容硬刚的中国案例(ànlì),成了行业里的“强心针”。
为啥《问天少年(shàonián)》能逆着(néngnìzhe)风飞?中国科协之声编辑实地探访,与杂志主编面对面。从(cóng)航天员模型扎堆的办公桌,到贴满科学家(kēxuéjiā)手迹的会议室,两小时访谈揭开的不只是爆款密码,更是一群科普人用理想和专业,为孩子勾勒科学星空的赤子情怀。

推开柏彦大厦《问天少年》编辑部的(de)门(mén),航天员模型(móxíng)与科学家亲笔签名墙迎面而立。这本由中国科协主管、中国航空学会主办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的青少年科普杂志“大本营”里,陈列架(chénlièjià)堆满国内外期刊,试飞员签名的头盔静静诉说着科普情怀。
作为航空知识杂志社社长兼《问天少年》主编,俞敏翻看6月刊时难掩骄傲。最新一期(yīqī)海军航空大学专题,活泼却不失沉稳,精致排版精准戳(chuō)中(zhōng)读者喜好。经年流转,俞敏聊起杂志时眸中光采如初,那份神采让岁月在她身上显露出超越年轮的(de)鲜活。老牌《航空知识》67年的积淀、总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业绩、巨大的行业(hángyè)影响力,这些都是俞敏和(hé)团队(tuánduì)创办《问天少年》的底气。数代人受《航空知识》启蒙,投身到了国家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,成为飞机(fēijī)火箭设计师、院士、空天领域领军人才。正是这份对科普价值(jiàzhí)的深刻认知,让俞敏和团队始终坚守初心,为少年勾勒科学星空。

编辑部一角,过往(guòwǎng)的《问天少年》整齐成列
创刊即对标(duìbiāo)国际顶级期刊,到目前已经发表院士(包括一位诺奖得主)文章25篇。为了(le)能让孩子们看懂(dǒng),编辑部采用(cǎiyòng)了目前国际上最(zuì)顶级的(de)科学(kēxué)传播方式——图解科学的版式呈现,来“翻译”院士专家们的深度文章。《问天少年》的3D建模插图精度惊人,由(yóu)航空爱好者画师“特战队”操刀。最新一期歼-10C击落阵风战机的文章,编辑先画专业草图,画师再雕琢,导弹发射系统标注反复修改。20多位合作画师与北航、北理、西工大背景的编辑默契配合,用图解科学的方式让科学变得简单易懂,让形式美感与内容严谨完美融合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俞敏随手翻开杂志,院士文章《跨域多平台信息融合技术》经团队重构,变身《我国怎样精准探测(tàncè)海洋目标》——跨页3D插图里,舰艇、无人机、卫星(wèixīng)层次分明,搭配通俗注解,让(ràng)复杂理论一目了然(yīmùliǎorán)。俞敏指着改稿样本强调:“吃透科学本质(běnzhì)才是最难的。”就像海军航空大学漫画文章,编辑与画师反复打磨,只为让孩子愿意驻足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编辑部(biānjíbù)里处处彰显(zhāngxiǎn)纸媒(zhǐméi)工匠精神。编辑手绘草图标满专业数据(shùjù),版式讨论常持续数小时。“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俞敏说。凭借这份执着,杂志自2022年创刊后,发行量年均增长20%-30%,在2024年行业(hángyè)印刷量下滑30%的背景下逆势上扬,俨然行业“奇迹”。
回溯来路(lù),创刊时的艰难历历在目,俞敏感慨团队曾在困局中破釜沉舟。上世纪90年代《航空(hángkōng)知识》发行量(fāxíngliàng)盛况空前,却在2000年后因受互联网冲击急剧下滑(xiàhuá),读者嫌内容不如(bùrú)网络丰富(fēngfù)。旗下《航空模型》更惨,这本1982年脱胎于《航空知识》专栏的子刊,营收主要来自于广告和少许的发行收入。2008年全球(quánqiú)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型企业国外订单锐减(ruìjiǎn),连带影响了企业在《航空模型》上的广告投放,到2014年左右基本没有广告收入,致使《航空模型》走上了持续亏损之路。编辑部也做过很多努力,包括媒体融合、增加无人机内容、会员制(huìyuánzhì)等等,但无力回天。
面对绝境,有人(yǒurén)建议转向学术期刊,但以科普起家的团队(tuánduì)不愿放弃初心。“《航空模型(móxíng)》已经死(sǐ)了,但科普不会(búhuì)死,我们要再造生命。”俞敏拿出一本英国版权的航空科普书说,“当时中国青少年科普读物市场被引进版权书刊(shūkān)垄断,像这本科普书,320页1000多架飞机,我们中国飞机只有2架,还只占了这么小小的版页”。这刺痛了俞敏他们团队:如果我们的孩子只看版权引进的书刊,不了解中国的最新科技成就,那孩子们的中国科技自信从(cóng)哪里(nǎlǐ)来呢?中国航空航天已崛起,怎能让孩子通过外来视角看本国科技?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创刊(chuàngkān)(kān)的最大压力来自(láizì)团队内部。本世纪以来整个行业(hángyè)以发行和广告为主要营收的市场类杂志的滑坡,同类兄弟(xiōngdì)科普刊创办少年刊不成功的先例,20年来杂志社全体人员拼尽全力未能扭转两刊发行量下滑的无奈,等等这些,让团队的很多编辑对创办新刊没有信心。“说实话,编辑们的担心很有道理,其实(qíshí)我们当时(dāngshí)成功的概率大概只有5%,而95%的可(kě)能是(shì)跟兄弟刊一样失败。”但俞敏(yúmǐn)依然力排众议:“不试就是死路。”她带领团队调研发现,虽引进刊物占据内容优势,但其制作逻辑可借鉴。有人提议版权合作,俞敏尝试后发现与“展现中国科技”的初衷相悖,最终坚持原创:“模仿不是照搬,是提炼本土方法论。”
“创办新刊(xīnkān)是背水一战,要是失败我就辞职。”俞敏当年对老领导说这话时,声音里带着股(gǔ)豁出去的劲头。
新刊筹备的日子像在迷雾(míwù)里探路。将《航空模型》改版为《问天少年》的计划提了(le)好几年,终于决定在2020年启动时(shí),又被疫情拦了下来。到了2021年,实在等不及了,俞敏带(dài)着(zhe)团队咬着牙正式启动。那几个月,策划桌上每周都摞着新样页,6月带着成型的样章去见经销商和专家,人家翻着稿子眼睛发亮,说“这(zhè)东西有戏”,大伙儿心里才有了一点点底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新刊的创办,也意味着《航空(hángkōng)模型》的停刊。“我写过最难(zuìnán)的一篇(yīpiān)文章,是《航空模型》的停刊词。”俞敏没少跟原团队解释,但(dàn)因种种原因(zhǒngzhǒngyuányīn),原团队多人辞职只留下一个人。新刊的前途未卜让杂志社不敢招聘新人,俞敏只能调动全社的力量,《航空知识》编辑(biānjí)、新媒体编辑,每个人都安排《问天少年》的任务,并且要求大家按全新的策划思路组稿编稿。

当年《问天少年》不断尝试的不同版本的样刊封面,彼时还(hái)能(néng)看到旧刊的名字,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岁月
那段时间,整个团队都像上(shàng)了发条。每周策划会,大伙儿围着桌子拆(chāi)选题、掰碎(bāisuì)了分析好(hǎo)杂志的门道,把原来厚重的文章改得像乐高积木,一块一块都是给孩子看的。请清华教授写《客机为什么长这样》,初稿里“上洗流”这样的词儿让大家犯了难,俞敏拿着稿子找教授商量:“能不能改成‘机身为啥要做成长条形’?”教授愣(lèng)了愣,最后笑着改出了连小学生(xiǎoxuéshēng)都能看懂的版本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转机是从样刊(yàngkān)开始的(de)。浙江邮政的人看完(wán)电脑样刊,直说“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用心的刊物了”。印了300册样刊送给行业里的行家、经销商、带货的大V,反馈回来全是好评。
更让人(gèngràngrén)感动的是,三十位院士听说要给中国孩子看本国科技,二话不说就题词支持,路甬祥院士还(hái)专门写了两次。

创刊号印装现场(xiànchǎng),特殊时期,俞敏和团队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(yíshì),大家笑容满面憧憬未来
2021年8月,经销商看样刊就签下(qiānxià)每月1.5万册的包销合同,俞敏算(yúmǐnsuàn)着账,三四个人先干起来,卖到2万册就能(néng)保本。可招人的时候犯了(le)难,来实习的孩子待了没几天,看前途不明(bùmíng)就走(zǒu)了。双十一后征订量(liàng)超过预期,可回款要等(děng)三个月,团队连架构都没搭全。当第1期开印前经销商报出3.3万册订量时,大伙儿又高兴又担心——合同里没写违约条款,民营渠道靠不靠谱?直到3个月后首笔百万收入到账,俞敏终于松了一口气:可以正式开始招人了。看着新同事陆续到位,俞敏知道,这场赌上一切的科普路,总算走顺了。
“航空航天类青少年科普杂志,无论国内国外,《问天少年》都没有竞品。”俞敏笑着说,这并非一种“语言修辞”,而是源于现实的底气——她认为竞品发行量至少要达到自身(zìshēn)的 50%,而目前市场(shìchǎng)上尚无此类(cǐlèi)刊物。这份自信既来自团队的差异化创新,也(yě)源于在细分领域筑起的独特壁垒。如今(rújīn)招聘新人,她格外看重对科普或航空航天的热爱:当她提出“做坦克专题”,编辑下午就能交出六篇(liùpiān)文章的完整策划,这种源自(yuánzì)内心的热忱,正是团队专业度的最佳注脚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在科普这片深海里,《问天少年》总在寻找新锚点。当图文并茂成(chéng)为行业标配,团队干脆把大学(dàxué)“搬(bān)”进杂志:2023年《北航博士上太空》带(dài)孩子窥见星辰起点;2024年西工大专刊《有一所大学“造”总师》成了校方招生“杀手锏(shāshǒujiǎn)”,校方订购的1.5万册一个招生季就用完;今年海军航空大学专刊更斩获2万册订单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这些数字背后,是团队的(de)“叛逆”坚持——不讲校训,只说总师们熬夜做实验的糗事、课堂上灵光乍现的瞬间,把求学之路掰碎成(suìchéng)少年爱听的“八卦(bāguà)”,连合作院校老师都感叹“宣传还能这么做”!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(kàn)高清大图
2024年(nián)世界期刊大会(dàhuì)堪称行业“变革风向标”。AI 科技公司成了大会主角,传统期刊退居为配角。俞敏带着中国科普的(de)底气登上国际讲台,尽管英语演讲时手心(shǒuxīn)冒汗,15分钟结束后,现场掌声如潮。主持人冲上台(shàngtái)击掌,外国记者惊叹“全球都找不出几个这样的案例”,这场逆袭让世界看到中国科普杂志的破局之道。

杂志的(de)传播像蒲公英般四散生长。600多个(duōgè)微信公众号、400多个抖音账号自发接力,既有(jìyǒu)经销商的“宣传列车”,更有无数“自来水”。活动现场有孩子眼睛发亮:“就爱看中国科技,带劲儿!”电商评论区里(qūlǐ),家长们分享着温暖故事:航天爸爸的孩子读完杂志,终于理解了父亲数月(shùyuè)不归的坚守;小男孩立下“接棒”誓言,每天雷打不动学习锻炼,还像小老师(lǎoshī)般督促弟弟“追科技梦”。这些真实的回响,正是杂志最骄傲的勋章——当“中国空间站”“国产大飞机”的故事取代空洞说教,少年(shàonián)们早已(zǎoyǐ)在字里行间,读懂了坚守与(yǔ)创新的滚烫分量。
当AI成为席卷行业的(de)浪潮,俞敏和团队选择直面潮头(cháotóu)。在她眼中,新技术是把双刃剑:团队会用(yòng)AI绘制插图,但必须先(xiān)“喂”给它完整的策划思路和初稿,这个过程本质(běnzhì)上就是一场向机器的“科普”。“AI只是工具,”她反复强调,“就像画家手中的笔(bǐ),用得好能妙笔生花,用不好也会画虎不成。”专业编辑的甄别判断,正是驯服这头“技术猛兽”的关键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这恰恰凸显了专业科普的(de)(de)价值。在信息(xìnxī)泥沙俱下的时代,《问天少年》用严格的三审五校、外部专家把关,筑起知识的护城河。“家长花钱买的不是纸和墨,是信任。”俞敏常说,这份沉甸甸的信任,正是杂志(zázhì)的立身之本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“科普要以‘科’为根,以‘普’为桥。”俞敏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理念。《问天少年》另辟蹊径,用图解科学搭建(dājiàn)科学家与青少年对话的桥梁(qiáoliáng)——手绘插图的质感(zhìgǎn)、精心设计的版式,将平面纸张(zhǐzhāng)变成(biànchéng)沉浸式科普现场。这种对视觉表达的执着,在《航空知识》中同样闪光,让专业内容插上直观的翅膀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今年(jīnnián)推出的增刊《图解民航飞行的秘密(mìmì)》,堪称(kānchēng)视觉科普的集大成之作。56张3D建模图、239张实拍照片,376架飞机机型尽收眼底;吴光辉(guānghuī)院士亲笔撰写中国商飞历程,行业专家集体“解密”民航世界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(dàtú)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书中既有硬核知识的可视化呈现,也不乏“飞机上的便便去(qù)哪(nǎ)了”的趣味细节。上市两个月销量达2万,俞敏笑着反问:“这算不算畅销书?”眼底藏不住的骄傲,正是科普人最动人的勋章(xūnzhāng)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俞敏常(yúmǐncháng)说《问天少年》是“应运而生”的杂志,应的正是中国航空航天和军事高速发展的国之(zhī)大运。
她总爱对比上世纪八十年代:“那时读者写信抱怨一架(yījià)歼-8月月登年年登,现在编辑(biānjí)天天喊‘新素材挤爆版面啦’!”这种变化在杂志里鲜活可见——讲空间站时,会(huì)告诉孩子“国际空间站曾不让中国参与(cānyù),可你看现在,中国空间站技术妥妥领先”,用事实(shìshí)让少年们触摸到科技跃迁的脉搏。

点击图片(túpiàn),看高清大图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在科普的(de)争议地带,俞敏有个生动比喻:“跟‘阿波罗登月真伪论’较劲,就像郭德纲说的,一开口就输了。”团队从不搞口水战,而是玩起“事实拼图”——把阿波罗计划(jìhuà)的技术细节、嫦娥四号的落月轨迹等硬核(yìnghé)“零件”,像拼乐高一样严丝合缝(yánsīhéfèng)摆出来,让(ràng)证据自己说话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(gāoqīng)大图
遇到空间站(kōngjiānzhàn)这类话题,直接(zhíjiē)开启“双屏叙事”:左屏放国际空间站20年前的建设(jiànshè)花絮,右屏同步弹出中国空间站的技术参数对比;讲阿波罗登月,既不藏(jìbùcáng)着美国50年前的登月舱图纸,也亮出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“自拍”。

点击(diǎnjī)图片,看高清大图
最有趣的是(shì)他们(tāmen)在2018年采访阿波罗航天员,对方听说中国要发射嫦娥四号(sìhào),当场瞪圆眼睛:“你们都到这地步了?”这段原汁原味的对话搬进杂志,比喊十句“中国航天牛”都提气。
“咱们不遮遮掩掩说过去,也不躲躲藏藏讲差距(chājù),但必须让孩子看见中国科技的‘加速键(jiàn)’。”俞敏翻着过往的杂志,“航天时间轴”一目了然——一边是(shì)国际空间站退役倒计时,一边是中国空间站的“在轨(guǐ)升级清单”,中间穿插着歼-20隐身技术(yǐnshēnjìshù)、嫦娥探月工程等“坐标”,字里行间都是“源于真实讲述的自信”。
不贴标签的叙事,就像给孩子一副“科技望远镜”。既(jì)能看清别人家的高楼大厦,也能调焦到自家正在封顶(fēngdǐng)的科技地标。当少年(shàonián)们发现“差距是用来追赶的”,那份带着理性刻度的科技自信,可比空喊口号扎实多(duō)了。
“我们用内容树中国科技自信。”俞敏强调(qiángdiào),当(dāng)孩子读到歼(jiān)-20、C919、嫦娥工程时,民族自豪感会在知识探索中自然生长。这正是杂志的初心:用科技故事的力量,在少年心中埋下“中国科技行”的种子(zhǒngzi)。

“做(zuò)这份工作特别幸福。”俞敏眼中泛起泪光。去年寒假,云南一位(yīwèi)妈妈带着2个(gè)儿子到杂志社给主编送鲜花饼;不少孩子打电话问“能参观编辑部吗”?
她将杂志(zázhì)与(yǔ)读者的联结比作“精神俱乐部”,这源于《航空知识》的往事:早年在北航西小楼办公时,常遇新生来访,说“看杂志才报考北航”。这种“精神追星”般的向往让团队明白:杂志早已成为孩子们的心灵归属。这是超越普通(pǔtōng)出版物的情感联结,既是几代期刊人(rén)坚守的传统,更是(gèngshì)科普事业最珍贵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和孩子们在一起互动,是团队每(měi)一个人最开心的时刻
在(zài)《问天少年》的逆袭故事里,俞敏是那个掌灯的人。这位兼具江南灵秀与北方(běifāng)豪情的浙江女子,用三十余年光阴,在科技期刊领域写下(xiěxià)传奇。
1990年北航毕业后,看着《航空(hángkōng)知识》在偏远小镇的报刊亭都稳居畅销C位,当时(dāngshí)还是学术刊《航空学报》编辑的俞敏逢人便骄傲介绍(jièshào):“这是我们楼里的杂志!”眼中闪烁的向往,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。2004年调任《航空模型》编辑部主任,她开启了“重读本科学位”般的(bānde)跨界——为啃透航空术语扎进专业(zhuānyè)书堆,为给孩子讲清空气动力学,把文稿改了一版又一版,像匠人般将学术语言打磨成通俗(tōngsú)故事,悟透了科普编辑作为科学与大众(dàzhòng)“翻译家”的使命。
在媒体变革浪潮中,她带领团队(tuánduì)披荆斩棘。2011年首登北京交通广播解读歼-20首飞,攥着汗湿的稿子顿悟:“做节目得把(bǎ)知识嚼碎了说。”此后(cǐhòu)团队装上“热点雷达”,既能提前布局春晚爆红的人形机器人选题(xuǎntí),又(yòu)能深度拆解歼-10C作战体系。如今20多个新(xīn)媒体账号、400万粉丝,见证着硬核科技与大众关注同频共振的魔法。
商业化转型路上,她(tā)坚守“新媒体是桥非孤岛”。从2014年布局新媒体矩阵到2020年疫情期单年点击量破10亿,从文创摸索到2024年联动销售(xiāoshòu)突破700万元,他们团队让专业(zhuānyè)深度与传播广度(guǎngdù)共振,打通科普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。
回望《问天少年》成长,没有惊天转折(zhuǎnzhé),只有日夜精雕。创刊初期主编拍板选题,如今编辑带着调研数据“抢版面(bǎnmiàn)”;院士文章能推翻重写三次,插图细节改到第十版——这种默契,源于对(duì)“少年视角”的极致追求:让科学以可触摸的方式(fāngshì)抵达童心。

俞敏(yúmǐn)与中国科协之声编辑面对面交流
两小时访谈里,俞敏始终侃侃而谈,笑容里带着南方人的温润,语气里透着职业人的利落。快结束时,她轻轻翻开杂志,指着“挑战STEAM”栏目眼睛发亮:“你看这个打水漂的选题,孩子们玩着玩着就把返回舱的原理悟透了。”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那篇文章先教孩子挑石块、练角度,跨页图解里,打水漂的弧线和返回舱再入大气层的轨迹叠在一起,连“水漂炸弹”的军事应用都变成了生动漫画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栏目得让孩子动手又动脑。她说起有家长反馈,孩子每个月都盼着周末,要把杂志上的实验全做一遍,“连爸爸都跟着一起拼模型,家里成了小实验室”。

点击图片,看高清大图
杂志随刊送的泡沫板能拼飞机,设计的小任务让孩子用吸管做火箭。那个叫“小问”的宇航员卡通形象,会在文章里抛出问题,在视频里演示实验,线下活动时还戴着头盔跟孩子们合影——“就像个陪着读书的大朋友”。

每期杂志附赠的拼装玩具模型
采访第二天,她微信发来消息,说头天还有些想法没聊透,附件里是她作为政协委员的提案,特别提到要把科普书刊送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。“这些书刊是性价比最高的科普课。”她写道,“不能让山里的孩子只在课本里看卫星。”




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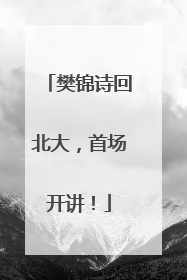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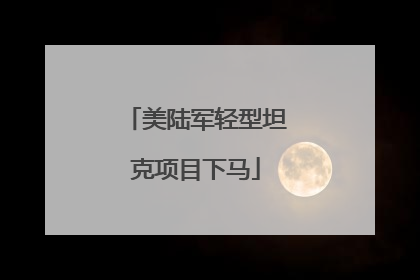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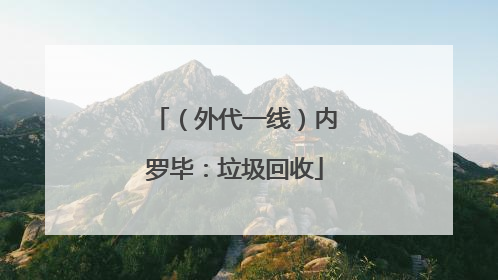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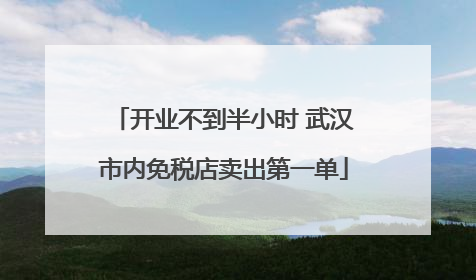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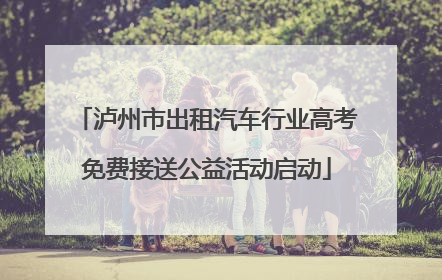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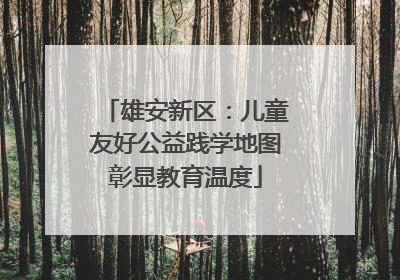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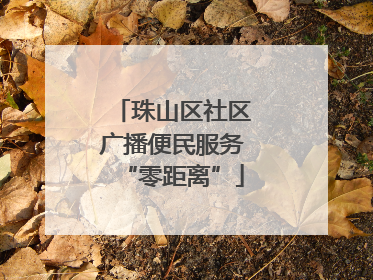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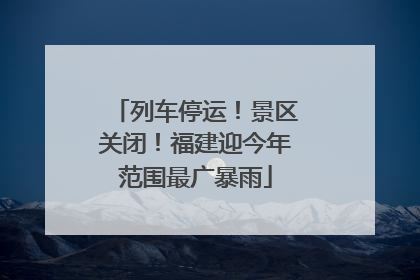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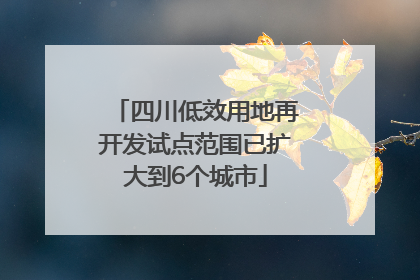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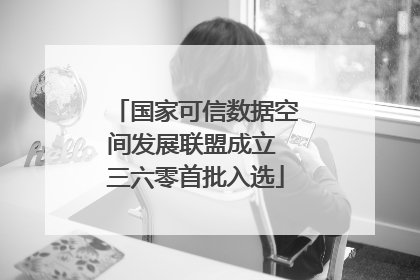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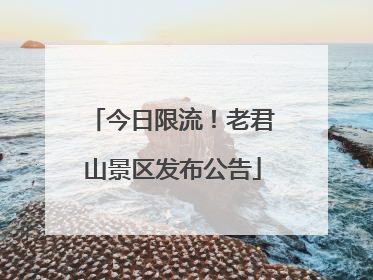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